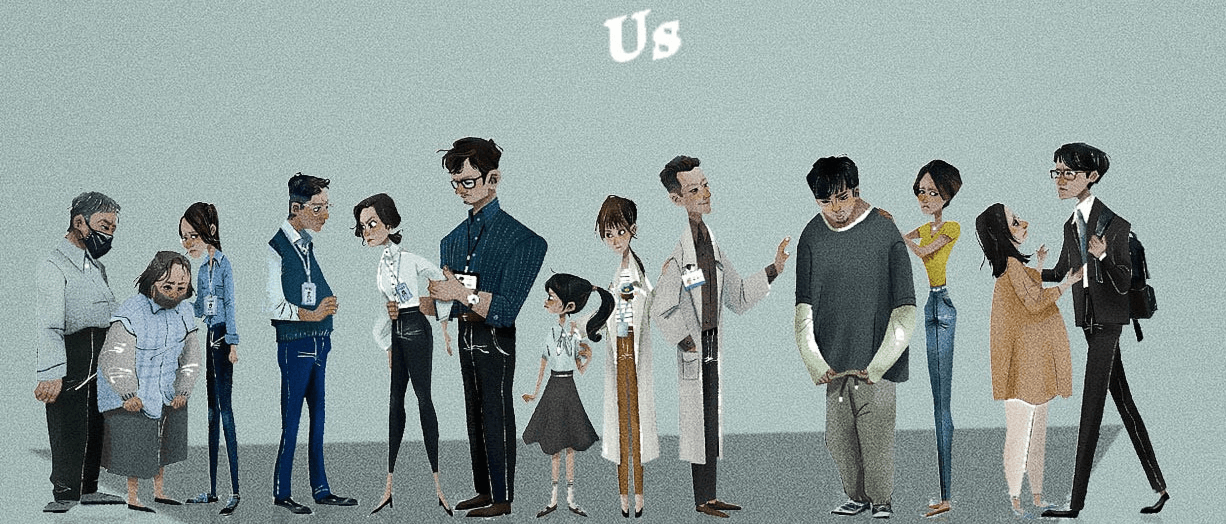我们都是“可恶”的“好人”——《我们与恶的距离》剧评(二)(完)
※ 本篇文章为2019年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的第二篇剧评,与第一篇剧评无直接关联,但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戳此处。
※ 本文全篇涉及剧透,虽然个人认为其对实际观看体验影响很有限,但对于剧透比较敏感的朋友请酌情考虑阅读。
世间上有很多种恶,如果以恶产生的原因来划分的话,有出于欲望的恶,就比如出自天主教而后又被很多艺术作品引用加工的七宗罪;还有来自于动物性本能的恶,例如一些极端环境下屈服于求生欲或生理需求而背弃人性的恶; 甚至,还有为实现与恶不直接相关的目标而在实现过程中产生的“手段之恶”……当然,更多时候我们产生恶的原因非常复杂,并不是单单来自于上述的某一个原因,而是某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然而这些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实施者是在拥有一种或多种“罪恶”的动机后,蓄意实施的“恶行”。
但在《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剧中,却充斥着另一种“恶”。这种“恶”虽然同样由人产生,但当ta施恶时,主观上并没有罪恶的想法或动机,即使此时他们已经造成了的不可挽回的伤害。正如剧中角色News哥所在和李大芝谈起她和宋乔安的冲突时所说,
我们都是好人,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既“来自于”我们,似乎又“不属于”我们的“恶”,究竟是什么?
极化的立场,极端的恶意
《我们与恶的距离》(后简称《我恶》)这部剧中虽然有很多条子故事线,但可以以随机杀人犯李晓明之死作为节点将整体剧情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的焦点之一即为李晓明的妹妹李大芝和她的上司、同时也是受害者母亲的宋乔安的冲突。分别是“加害者家属”和“受害者家属”两个完全对立身份的人,从一登场就似乎向观众预示着,她们之间必将有一场“大战”。
于是,当剧集铺垫了5集后,宋乔安终于在李晓明被提前执行死刑枪决、李大芝濒临崩溃之际,意外发现她的真实身份;而后宋乔安派人尾随李大芝,使得还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李氏家人再次被媒体曝光,而李大芝也一气之下来到公司和宋乔安当面对质。
客观来说,宋乔安在没有经过李大芝的知悉和允许下,派记者尾随并强行采访李大芝和她的家人,是存在程序合理性的问题的;而宋乔安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将自己的个人恩怨带入到工作中也有失专业水准。此外,媒体持续追踪报道加害者家属这件事,至少站在李大芝一家人的角度是“不道德”的。哥哥李晓明虽然拒绝精神鉴定,但是被怀疑拥有极端自恋型人格,案发之后他也一直拒绝联系家人,主动断绝关系。最后,不论李大芝一家人对李晓明变成这样有多少间接的影响,做出这样决定,并付出行动的,只有李晓明自己,他们对他的作案计划一无所知,法院也没有判定他们和案件有任何关联。
但即便如此,李大芝和他的父母,还是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全民公敌……而在艰难熬过两年、终于决定面对一切,并在王律师的帮助下得以见李晓明一面之时,政府却为平民愤而“突发”执行李晓明的枪决,而他们也再次遭到媒体曝光骚扰。虽然他们努力想要“赎罪”,宋乔安的“品味新闻”却将他们宣传成“想跟加害者做切割”……难道就因为有一个变态杀人魔,家里剩下的人就没有活下去的权利吗?这些“无良媒体”的所作所为,宋乔安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恶”吗?
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站在此时宋乔安,以及很多其他备受折磨的受害者家属的立场上看,整个事件似乎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现代法律在制定时往往会结合多种法学流派,判决时也往往会考虑道德正义、法律程序以及社会影响等多个因素[1]。但事实是,法律永远不是完美的,更不用说有时因为法律本身的漏洞或社会系统性的局限,法律的判决根本就不合理。
而对于这样一个用自制枪械随机射杀9人并造成21伤的极端案件,判处凶手李晓明一个人死刑,就可以结束了吗?且不论这个事件造成的社会冲击,那些因此一辈子忍受残疾的受害者,以及永远痛失亲人的家属,就该认命吗?就像宋乔安在第三集中跟丈夫刘昭国吵架时所说的一样:
挪威社会福利这么好,还不是出了随机杀人犯?我们的社会安全网,我们的教育体制,永远控制不了那些加害者!
如果法律和社会制度无法给予这些受害者足够的“正义”,身居新闻媒体行业的、同时作为受害者家属的她,又怎能“坐视不管”?
一边是想要“赎罪”而不能,反被逼到死角的李大芝;另一边是想要“忘却”而不能,唯有视工作为战场的宋乔安,她们在旁人眼中是那么“可怜”,在对方眼中却是那么“可恨”。而这一切,只因2年前的那场悲剧,如万丈深渊将她们分隔在两端,一边是“加害者家属”,另一边是“被害者家属”。
而如果如此极端且对立的双方无法得到和解,她们诞生的恶意只会愈演愈烈——带来更深的伤害,波及的更广的范围。和宋乔安对峙后的李大芝再次失去生活的希望,将自己关在房东家中,也不接父母的电话;而被李大芝在公司当众控诉“媒体杀人”的宋乔安,没多久就得知一名初中生与母亲争吵后砍伤7人并高呼“李晓明万岁”的消息。此时虽然宋乔安已经开始有些动摇自己此前的报道行为是否对于社会造成了更多的负面影响,但还是做了两则新闻。然而,当众多媒体将这个小孩定性成“李晓明模仿犯”之后,孩子的母亲在网络上发了一个视频——控诉媒体不去报道孩子有轻度智能障碍以及在学校受到霸凌的事实,直言“媒体就是在杀人”。虽然事后媒体求证孩子确实有相关疾病,母亲还患有抑郁症,但为时已晚,警方在海岸边发现了他们跳崖自尽的尸体。
在媒体再次曝光带来的社会压力下,李大芝又会像两年前一样什么都做不了,而就算李大芝不会因此转而报复社会,也可能因此一蹶不振,甚至成为击垮父母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宋乔安不仅很可能会一步步葬送自己的事业,甚至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继续伤害自己的同事,自己的家人,以及更多社会上根本素不相识的人。
值得庆幸的是,与他们一起面对的还有家人和朋友。房东应思悦在知道了李大芝的真实身份后,也没有对她有丝毫的忌惮,还主动邀请她去自己的奶茶店里打工;李大芝的父母在News哥和王律师的帮助下终于和她取得联系,不再担心;而News哥更是亲自来探望她,提出愿意给她介绍其他新闻工作的机会。而在宋乔安这边,她的丈夫刘昭国不仅主动试图改善婚姻关系,还一步步帮她走出当年痛失儿子的内心阴霾与愧疚;李大芝正式离开公司时向她敞开心扉,并诚心道歉;以及News哥、公司同事以及李大芝等人对于新闻媒体的观点,让她重新思考做新闻的那份初心。
思悦姐、父母还有News哥的鼓励与理解,让李大芝重新记起,自己并非只能做一个没有价值、被人唾弃的“加害者家属”;而李大芝、丈夫刘昭国还有News哥的真诚与启迪,也让宋乔安意识到在“受害者家属”之前,自己更是一位媒体人。也许就像宋乔安之后所说,她和李大芝这辈子依旧不可能做朋友,但至少当她们不再将自己拘束于“加害者家属”和“受害者家属”这两个极端又针锋相对的立场中,彼此之间的恶意,以及有这份恶意产生的“恶”,都在渐渐淡去。其实,这份和解不仅是和彼此的和解,更是跟自己的和解。有时候你把自己逼到了角落里,就会觉得世界都在针对你;而处于“沟壑两端”的人,彼此眼中,皆为恶人。
“真相”越远,恶意越深
如果说前面的“恶”是围绕“当事者”的“极化”的话,那么另一种“恶”便是来自于“旁观者”的“无知”和“傲慢”。“无知”指的是信息上的缺失, 而“傲慢”指的是在信息不足或有偏差的情况下便轻易下结论和表达观点。
其实这种“恶”在整部剧中最直观的一个体现,便是来自媒体传播的“恶”:媒体为了追求新闻时效性和吸引力而妥协全面性、客观性和真实性的行业潜规则;以及网民在看到片面信息、或片面理解信息后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网络常态;更可怕的是两者互相影响、恶性循环。关于这方面的分析我在第一篇剧评中有专门的讨论。
但即使我们现在不去考虑那些无良媒体和片面新闻,而是着眼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还是会发现人与人之间,在不断产生着类似的“恶”——公司里同事之间不符事实的流言蜚语、领导对于员工压力和意见的“熟视无睹”、特殊家庭背景的学生在学校遭受的霸凌……固然,这其中有些恶行是蓄意的,它们不在讨论范围之内,但剩下的那些“不自觉”的冷漠、偏见与歧视,不也是一种不够了解或不够理解,却视自己行为理所当然的“无知”与“傲慢”吗?在我看来这种因为远离“真相”,而产生的“恶”,实际上是一种缺乏同理心而导致的“恶”。
很多人经常将同理心(Empathy)[2]、同情心(Sympathy)[3]这两个概念搞混,但事实上,它们的定义有一定的区别。
同情心一般仅针对情绪而言,指的是可以感知对方的情绪做出相对回应的能力,通常是指回想自己有关的认知和经历,由此产生相应的情感反馈,不一定与对方的感受一致。而同理心(也叫共情),则更在于你能够切身体会对方的感受和心理,重点在于“站在对方的角度”。具体而言,同理心可以分为三大类:情感同理心(Affective Empathy)、认知同理心(Cognitive Empathy)和躯体同理心(Somatic Empathy)。躯体同理心一般用于描述在特定情况下由于精神作用引起生理反应(如疼痛)的能力或现象,不是本文的主要讨论范围,而情感同理心和认知同理心则可以理解为“在感情上做到‘感同身受’”和“在理性上做到‘换位思考’”。
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我恶》,就会发现剧集中律师王赦的故事,恰恰是在讨论这种缺乏同理心所导致的“恶”。王赦一出场的时候,其实显得非常“圣人”:他帮助精神病罪犯这个非常“特殊”的弱势群体做刑事辩护律师,不仅工资赚得少,还要承受社会上的舆论压力和极端人士人身攻击(甚至是物理攻击)。但是对此,他却一副淡然自若的样子:在大街上被受害者家属泼屎一点也不生气;回家后会哄妻子,让她不要担心自己;而面对已经过去了两年、当事人和家属都已经放弃的案子(李晓明案),他还坚持寻找突破……简直与其他在这个残酷世界中挣扎的角色显得格格不入。而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并非被动卷入这些事件,而是主动参与进来——不仅自愿接下精神病杀人犯陈昌的案件,而且还在应思聪私闯自己女儿所在的幼儿园被抓后,申请成为他的辩护律师……这个“过于”大公无私、泰然自若的律师,虽然值得人尊敬,但我相信许多观众朋友在初见他时,也和我一样,不免觉得他有点“假”。
果不其然,不仅观众“受不了”,就连剧中王赦的妻子丁美媚也忍受不了丈夫这种“为事业牺牲家庭”、“还帮变态逃过死刑”的“混蛋律师”,带着他们的女儿搬回了娘家住。甚至当王赦带她去见陈昌的母亲时,听到那位母亲还一心只想着把陈昌保出来,希望“花钱了事”,让她更觉得不可思议。于是,王赦终于对妻子说出了自己一直以来的秘密——他自己也差点成为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罪犯,仅仅因为自己当年的“倒霉”而侥幸“错过”,而曾经的作恶机会和冲动,正是来源于自己悲惨而糟糕的成长环境,如同陈昌曾经经历的一样。
一个人究竟能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外在的各种“机缘巧合”是否才是决定了我们的真正原因?这个问题过于复杂,也不是本剧的核心命题。但我现在至少明白,为什么王赦在之后刻苦读书,成为了专为精神病等社会少数群体辩护的刑事律师,我也终于理解,为什么即使是整个社会愤恨不平、网络上谩骂不断,他也不愿意称这些罪犯为“坏人”——因为他在感性上,得以体会这些人经历过的痛苦、感受过的无助;又在理性上,能够明白这些折磨会产生多么大的负面影响。于是他意识到:如果把这些人当成普通罪犯一样去审判和对待,看似更加节约成本(没有医疗费用),也更加顺应民意(没有死刑豁免),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不会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相反,只有找到每个精神病罪犯犯罪背后的社会性原因,同时保障他们的基本人权,才能引起政府的重视、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从而避免更多悲剧的发生。而这份始于感性,经由理性的同理心也成为了他坚持这份正义事业的原动力。
可是,反观那些缺乏同理心的人们呢?他们不仅无法意识到这些精神病罪犯的“悲剧性”,更无法理解王赦这么做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和价值。相反,他们将这些精神病罪犯直接贴上“变态”的标签,将“保护”这些“变态”的律师视作“混蛋”——哪怕远到素未谋面的普通网民,亦或近到亲密无间的妻子,他们的“样子”正如王赦所说:
……你们这些人,遇到这些事,只有愤怒、害怕,你们胆怯,你们根本“没有机会”去了解他们背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当我们在对一些事物指指点点、高谈阔论,甚至义愤填膺的时候,我们真的有做到“旁观者清”吗?因为“旁观者清”绝对不是一种不去调查、体会、思考背后“真相”就给当事人贴标签、给事件下结论的行为,更不是一种“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的态度。到头来,这种缺乏同理心的“旁观者”并没有比“当事者”看的更清楚或更全面,仅仅是在简单粗暴地“管中窥豹”罢了。这是一种“旁观者”的“无知”,更是一种“旁观者”的“傲慢”。
但事情到此远还没有结束。这种来自“无知”和“傲慢”的“恶”最可怕的地方在于,恶意往往会随着“真相”的远离而逐渐加深。身为精神病医生的林一骏虽然一开始有“王赦是拿钱办事”的偏见,但是对他的恶意并没有普通人那么深。这是因为他的工作经历和专业知识,使他对王赦的同理心比普通人强:一方面在感性上他更能体会精神病患者的痛苦,另一方面在理性上他也更能理解王赦这么做的合理性。但是对于剧中那些离“真相”更远的人,他们产生的恶意和伤害可要大得多——自诩正义的“热心网友”不断骚扰、谩骂王赦和他的妻子;自称“并非歧视”的市民却因“怕精神病患者的‘危险’而不敢去公园”这样的理由去抗议康复之家设立在社区附近(剧中有指出非精神病犯罪率不比精神病低);为了追求“新闻价值”的媒体一得到发现母子尸体的消息便火速赶到现场去报道,还视刚刚经历丧妻丧子之痛的丈夫为完善报道的素材……以及迫于社会舆论压力而对李晓明提前执行的死刑枪决,正是屈服于这种“恶”最极端而又讽刺的体现。死掉的,确实只是一个该死之人,但陪葬的,是整个社会的法治精神。
退一步讲,确实,即使我们主观上有意识地去体现同理之心,我们对于事物的认知和理解是还会受到外界信息的影响,它们可以“拉伸”我们和“真相”的距离,甚至还可能“改变”“真相”本身。而互联网作为我们的主要信息来源,进一步放大和加剧了这个效应,以至于它最终的效果是正向还是负向,依旧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议题[4][5]。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有时候,阻碍我们“去听”、“去看”、去寻找“真相”的,并非那些外在的客观条件,而是我们内在的主观选择:网络暴力,这个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现象,不正是这种我们“自作自受”的恶果吗?实施网络暴力的人不仅不会换位思考,考虑他人的感受,还会用非平等、破坏性的方式(辱骂、煽动粉丝、恶意举报等)去“抹杀”对方的存在,以“确保”自我认知的“主宰”。但最关键的是,他们是主观抛弃了同理心,自愿拥抱了来自“虚拟暴力”的快感。这样的人离恶已经近在咫尺,而那些蓄意实施或煽动网络暴力的人,则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恶人了,只不过他们现在还很难受到法律的制约。
“心”之距离与“恶”之距离
我虽然认为《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剧非常优秀,但实际上我的观看体验并不舒服,甚至可以说非常痛苦。这份痛苦不仅仅来自于剧集中那一个个既真实又沉重的案件和转折,更来自于每个主要角色的纠葛和挣扎,以及这背后带给我的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这份无力感其实还是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来自剧集创作者的发问:“我们都是好人,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而在分析了上述两种我认为是“罪魁祸首”的“恶”之后,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也变得清晰起来。这两种我们不得不打上引号的“恶”,其实都可以归因于人心与人心之间的“距离”——隔阂。
隔阂会将我们置于不同的立场,也会让我们无法、甚至不愿去真正理解对方。有时,隔阂存在于两个人之间,有时它也可以存在于两群人之间,有时它还可以是一个人和一群人之间的。一个隔阂既可能是有意设立的,也可能是无疑形成的,一个薄弱且具体的隔阂可能只需要一句话便可以被破除,但一个强烈或复杂的隔阂或许只会在岁月流逝中愈发“坚固”。有时候我们急切地渴望打破隔阂,也有时候我们把它当成自己的堡垒 ……但不变的是,只要隔阂存在,即使没有“恶人”,“恶”也会不断出现,而当隔阂越大,这股恶意也越深,隔阂越多,这份恶意扩散得也越广。
那么产生隔阂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究竟有没有一个办法可以从根源上彻底消除隔阂?现实生活的种种遭遇,不由地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而历史上的创作者们也不断通过电影、动漫、游戏等各种形式的艺术作品来表达自己对于这个命题的诠释和思考,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依旧没有一个公认且实际的答案。
由于《我恶》剧情和人物极大的真实性和现实性,我原本期待创作者们最终会给出一份怎样的“答案”,但结局却让我“失望”了。在狂风暴雨的黑暗中,我没有看到指引方向的灯塔,也没有看到惊天动地的毁灭,等来的只是雨过天晴的平静与黎明。但当我开始写这篇影评,回首整部作品时,我终于意识到——《我恶》的“现实”并不是为了给出一个同样现实的“人类补完计划”,而是要以最感性,也最理性的方式,来体现“提醒”的力量:一种包含善意、同理心和建设性意见的“提醒”。
的确,“提醒”一直以来都像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因为“提醒”从来都不能保证“悲剧”不再发生,也不能保证“希望”就会出现。而对于“隔阂”这个可能永远无法一劳永逸的难题,这种“提醒”似乎是一种走投无路的挣扎。但如果不断、不断、不断地“提醒”,这个挣扎也许就会变成匍匐,然后变成一点、一点、一点的前进,去冲破那些使我们远离彼此的隔阂,以及它们所创造的“恶”。回首《我恶》——正是在许多“贵人”不断的“提醒”下,李大芝才逐渐走出“加害者家属”的阴影,但同时勇敢地面对依旧残酷的社会,正是在家人和同事不断的“提醒”下,宋乔安才逐渐撕下“被害者家属”的标签,重拾一个新闻媒体人的骄傲,也正是因为王赦对自己和他人不断的“提醒”,他才能够“独自”在这份正义事业上坚持那么久,也能在被现实击垮后再次得到周围人的“提醒”,继续坚持下去……最终得以让两年前李晓明案的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属愿意坐下来和李大芝一家进行修复式会谈。而最后应思聪在整部剧中的故事,同样是在“提醒”我们,在每个人的不断努力下,他没有成为另一个李晓明或陈昌。即使新的隔阂在不断产生,新的恶意在继续传播,互相帮助和不断的“提醒”,确实在让这个苦中带甜的“未来”一点点变好。
因此,当你看完这篇长篇累牍的剧评,却发现我给不出类似“42”一样惊世骇俗的结论时,我只希望没有让你太过失望。毕竟我想做的,只是通过一个小小的“提醒”,扶一把被这个残酷社会“打趴下”的朋友们,然后一起大声冲着世界喊出“哈哈哈”!这不就是生活嘛,你说对吧?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参考
我们都是“可恶”的“好人”——《我们与恶的距离》剧评(二)(完)